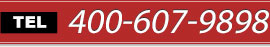日本铁壶的着色是素淡的,这符合日本文化中“寂”的色彩。
“寂”这一概念的深层的意义,就是“老”、“古”、“旧”。本来,“寂”在日语中,作为动词,具有“变旧”、“变老”、“生锈”的意思。这个词给人的直观感觉就是“黯淡”、“烟熏色”、“陈旧”等,这是汉语中的“寂”字所没有的含义。如果说,“寂”的第一层含义“寂静”、“安静”主要是从空间的角度而言,与此相关的“寂然、寂静、寂寥、孤寂、孤高”等状态与感觉,都有赖于空间上的相对幽闭和收缩,或者空间上的无限空旷荒凉,都可以归结为空间的范畴。而“寂”的“变旧”、“生锈”、“带有古旧色”等义,都与时间的因素联系在一起,与时间上的积淀性密切关联。
“寂”的这种“古老”、“陈旧”的意味,如何会成为一种审美价值呢?我们都知道,“古老”、“陈旧”的对义词是新鲜、生动、蓬勃,这些都具有无可争议的审美价值。而“古老”、“陈旧”往往表示着对象在外部所显示出来的某种程度的陈旧、磨灭和衰朽。这种消极性的东西,在外部常常表现为不美、乃至丑。而不美与丑如何能够转化为美呢?
一方面,衰落、凋敝、破旧干枯的、不完满的事物,会引起俳人们对生命、对于变化与变迁的惋叹、感慨、惆怅、同情与留恋。早在14世纪的僧人作家吉田兼好的随笔集《徒然草》第八二则中,就明确地提出残破的书籍是美的。在该书的第一三七节,认为比起满月,残月更美;比起盛开的樱花,凋落的樱花更美;比起男女的相聚相爱,两相分别和相互思念更美。从这个角度看,西尾实把《徒然草》看做是“寂”的审美意识的最早的表达。
在俳谐中,这种审美意识得到了更为集中的表现。例如,看到店头的萝卜干皱了,俳人桐叶吟咏了一首俳句:“还有那干皱了的大萝卜呀!”松尾芭蕉也有一首俳句,曰:“买来的面饼放在那里,都干枯了,多可惜呀。”这里所咏叹的是“干皱”“干枯”的对象,最能体现“寂”的趣味。用俳人北枝的一首俳句来说,“寂”审美的趣味,就是“面目清癯的秋天啊,你是风雅”。在这个意义上,“寂”就是晚秋那种盛极而败的凋敝状态。俳人莺笠在《芭蕉叶舟》一书中认为:“句以‘寂’为佳,但过于‘寂’,则如见骸骨,失去皮肉”,可见“寂”就是老而瘦硬甚至瘦骨嶙峋的状态。
莺笠在《芭蕉叶舟》中还说过这样一段话:“句有亮光,则显华丽,此为高调之句;有弱光、有微温者,是为低调之句。……亮光、微温、华丽、光芒,此四者,句之病也,是本流派所厌弃者也。中人以上者若要长进,必先去其‘光’,高手之句无‘光’,亦无华丽。句应如清水,淡然无味。有垢之句,污而浊。香味清淡,似有似无,则幽雅可亲。”这里强调的是古旧之美。芭蕉的弟子之一森川许六在《赠落柿舍去来书》中写道:“我就要四十二岁了,血气尚未衰退,还能作出华丽之句来。随着年龄增长,即便不刻意追求,也会自然吟咏出‘寂、枝折’之句来。”可见在他看来,“寂”是一种自然而然的“老”的趣味。
但是,仅仅是“老”本身,还不能构成真正的“寂”的真髓,正如莺笠所说的“过于‘寂’,则如见骸骨,失去皮肉”。假如没有生命的烛照,就没有“寂”之美。关键是,人们要能够从“古老”“陈旧”的事物中见出生命的累积、时间的沉淀,才是真正的“寂”之美。这就与人类的生命、人类的生命体验,产生了一种不可分割的深刻联系。任何生命都是有限的、短暂的,而我们又可以从某些“古老”“陈旧”的事物中,某种程度地见出生命的顽强不绝、坚韧性、超越性和无限性。这样一来,“古老”“陈旧”就有了生命的移入与投射,就具有了审美价值。最为典型的是古代文物。有时候,尽管“古老”“陈旧”的对象是一种自然物,例如一块长着青苔的古老的岩石、一棵枝叶稀疏的老松,只要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时间与生命的积淀,它们就同样具有审美价值。